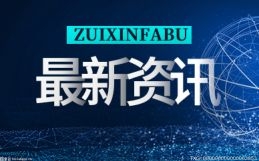《万岁通天帖》岳珂提到最初王方庆呈献给武则天的家族墨宝一共有十卷,包含王导以下王氏家族一共二十八个人的墨迹。岳珂也特别详细纪录在宋代就已经佚失的部分,其中包括有十一代祖王导,十代祖王洽,九代祖王珣,八代祖王昙首,七代祖王僧绰,六代祖王仲宝,五代祖王骞,以及王方庆的高祖王规,曾祖王褒,一共九代九个人的作品。
从岳珂的跋文来看,《万岁通天帖》的价值不只在其中有赫赫有名的王羲之、王献之的墨宝,更值得重视的应该是《万岁通天帖》完整呈现了王氏家族从东晋通过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,一直到入唐将近三、四百年间书法风格的演变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东晋至隋唐统一,经历三百多年南北朝分裂。南北朝不只是“五胡乱华”,数百年间,烽烟四起,人命如草,生灵涂炭,正是流离颠沛的年代。在那一时期,朝代兴亡,野心政客彼此争斗,政权迭起,时间都不长久。而王世一族,人才辈出,可以在如此长的数百年间传承书法,没有中断,或许是阅读《万岁通天帖》时特别应该注意的问题。
在那样的年代,一个家族担负起了稳定南方的责任,从王导辅佐东晋王室建国,到下一代,下下一代,在偏安的岁月,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,可以吟诵诗书,可以走在云淡风轻的山水中,可以与亲友倘佯周旋,可以书信往返,可以写出优雅安静的心事,可以相信文化的力量更大过于政权,可以通过一次一次朝代兴亡,相信有更长久的东西,因此传承着没有中断的文化理想,传承着生命价值笃定的信念,传承着美,传承着生命之爱。
阅读已经残缺不全的《万岁通天帖》,或许可以对一部颠沛流离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有更深刻的领悟。
《廿九帖》 东晋 王献之
辽宁博物馆藏
《万岁通天帖》里有王献之的《廿九帖》,——“ 廿九日,献之白。昨遂不奉别,怅恨。深体中复,何如。弟甚顿,匆匆,不具。献之再拜。 ”
王献之的书法历来就被常拿来与他的父亲王羲之比较,做为一代书圣的下一代,在书法上的表现,一方面不能不受父亲影响,另一方面,又必须从前人阴影中走出,创立自我风格,大创作者的第二代因此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辛苦。
《万岁通天帖》里有王羲之五子王徽之的《新月帖》,书体与王羲之非常接近,在书法史上,王徽之也不被认为是有独创风格的大书法家。
其实以《廿九帖》来观察,王献之的书风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父亲影响,安静平和,笔势平稳内敛,不像书法史上说的那样飞扬。
魏晋人喜欢品评人物高下,在《世说新语》“品藻”一章有极好的记载——谢安问王献之:你的书法跟父亲比,哪个好?王献之回答:“固当不同。”谢安继续逼问:外人好像不这样看。王献之说:“外人哪得知!”
王献之的回答完全合于现代美学艺术创作的自我完成。本来父子创作,个人有个人的风格,也难以比高下。王献之不愿意比较自己与父亲书法的优劣,只是说:“ 不同 ”,但是当谢安用舆论逼问,抬出“外人”来贬抑王献之时,王献之就不客气地回答:“外人哪得知!”王献之对自己的创作充满自信,认为艺术创作到了高深处,“外行人”哪里能懂。也藉此把谢安这一类政治人物的粗暴主观一句话顶了回去。像谢安一样习惯用第一名第二名的排序来看艺术创作的人当然不少,唐太宗也是其中之一,他们习惯了政治圈的争强斗胜,习惯用非赢即输来看待人生,在美学宽容的领域往往就捉襟见肘,少了坦荡自在,也少了宽阔豁达。
《鸭头丸帖》 东晋 王献之
上海博物馆藏
王羲之古典、静穆、收敛,以楷行为主,从容潇酒;王献之的《鸭头丸帖》、《新妇地黄汤帖》,米芾临的《中秋帖》都看到他完全不同于父亲的风格,笔势变化更多,线条流走速度更快,以行书走向狂草,更多书写上的自由,创立书法史上的“一笔书”,打破独立的字的结体,更重视字与字之间气的流动贯通,王献之的创新性,同时代的谢安不了解,三百年后的唐太宗也不了解。
唐太宗极力赞扬王羲之,贬抑王献之,并没有一定的道理,他全力搜求王羲之作品,好像是看重美,却流传出“萧翼赚兰亭”这样以诈骗手段霸占“兰亭”的可笑故事,爱美,结果演变成贪婪,其实可悲。
手上有权力,权力却常常正是执着偏见的开始,也使唐太宗无法同时看到王羲之、王献之的“不同”,“不同”正是美学可贵之处,“美”其实不是辩论,勿宁更是一种领悟,一种陶醉,一种欢喜与赞叹。
王献之被唐太宗贬抑,影响初唐一代书法界对献之书的态度,一直到盛中唐,狂草的出现明显祖述王献之书风,走向更个人表现,更浪漫、更自由挥洒、更恣肆狂放的书风,王献之的美学风格也在长期被忽略之后,在北宋得到了米芾这一真正的知音。
书法史上常常说王羲之“内擫”,王献之“外拓”,很精简的两个美学词汇,但说得真好。“内撒”是向内收敛,以含蓄为美;“外拓”是向外开展,以奔放为美,两种风格,并无优劣,的确只是“不同”。